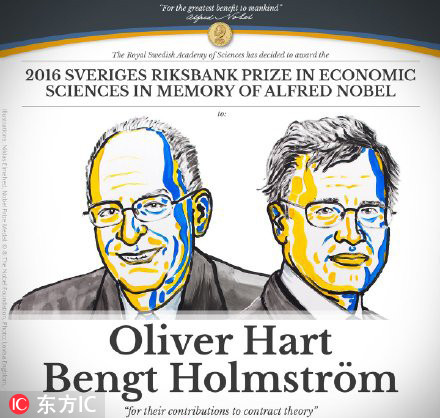
中國日報網(wǎng)10月11日綜合(涂恬)斯德哥爾摩時間10日上午,瑞典皇家科學(xué)院正式宣布,將2016年諾貝爾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獎授予奧利弗·哈特和本特·霍姆斯特羅姆,以表彰他們在契約理論方面的研究貢獻(xiàn)。
諾貝爾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獎評選委員會當(dāng)天發(fā)表聲明稱,兩名獲獎?wù)邉?chuàng)建的新契約理論工具對于理解現(xiàn)實生活中的契約與制度,以及契約設(shè)計中的潛在缺陷十分具有價值。據(jù)悉,兩位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家將平分今年的諾貝爾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獎獎金,總額為800萬瑞典克朗(約合93萬美元)。
那么,究竟什么是契約理論?這兩位獲獎的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家又分別對契約理論的發(fā)展做出了什么樣的貢獻(xiàn)?契約理論在現(xiàn)實的經(jīng)濟(jì)活動中,又能夠發(fā)揮什么樣的作用?
接下來就讓我們來詳細(xì)為您解密今年諾貝爾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獎“關(guān)鍵詞”——契約理論。本文正文共有2405個字,閱讀全文需要十分鐘。

契約理論是什么?
資料顯示,“契約理論”是研究在特定交易環(huán)境下來分析不同合同人之間的經(jīng)濟(jì)行為與結(jié)果,往往需要通過假定條件在一定程度上簡化交易屬性,建立模型來分析并得出理論觀點。由于現(xiàn)實交易通常具備復(fù)雜性,很難由統(tǒng)一的模型來概括,由此形成了從不同側(cè)重點來分析特定交易的契約理論學(xué)派。“契約理論”也是近30年來迅速發(fā)展的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分支之一,一直處于不停的整合過程之中。
諾貝爾官網(wǎng)對此也有所解釋:“契約理論”是用來解決類似這樣的問題的:諸如學(xué)校、醫(yī)院和監(jiān)獄這樣的公共服務(wù)的提供者,應(yīng)該是國有的還是私有的?教師、醫(yī)生和獄卒應(yīng)該拿固定工資,還是績效工資?企業(yè)管理人員的收入應(yīng)當(dāng)多少來自獎金,多少來自認(rèn)股權(quán)?
那么,契約理論的研究者們?yōu)楹文軌驍孬@今年的諾貝爾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獎?在解釋獲獎原因時,諾貝爾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獎評委會主席皮爾·斯特倫姆伯格表示,現(xiàn)代社會契約無處不在,并且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。小到個人借貸的貸款合同,員工的雇傭合同,大至公司之間的合作協(xié)議,甚至是國家之間簽訂的貿(mào)易合作協(xié)議。這些都是契約的一種形式,而正是因為契約的普遍性和重要性,今年諾貝爾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獎得主哈特及霍姆斯特羅姆對契約研究所作出的貢獻(xiàn)才顯得至關(guān)重要。他們對契約理論的發(fā)展被廣泛的運(yùn)用到現(xiàn)代企業(yè)的激勵機(jī)制,企業(yè)合并等領(lǐng)域,甚至可以為國家政策制定者提供理論基礎(chǔ)。
兩位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家的研究成果
具體來看兩位獲獎?wù)叩那闆r,其中奧利弗·哈特是美國哈佛大學(xué)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教授,1969年從劍橋大學(xué)國王學(xué)院獲得數(shù)學(xué)學(xué)士學(xué)位,此后他又轉(zhuǎn)向了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,并于1972年從英國華威大學(xué)獲得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碩士學(xué)位,1974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(xué)獲得博士學(xué)位。此后他曾返回英國在劍橋大學(xué)、倫敦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院等知名院校任教。1984年,奧利弗·哈特又來到美國出任麻省理工學(xué)院的教授。整整十年之后,奧利弗·哈特又轉(zhuǎn)到哈佛大學(xué)。
哈特關(guān)注契約理論、企業(yè)理論、公司金融和法律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等研究領(lǐng)域,是合同理論、現(xiàn)代廠商理論和公司財務(wù)理論的創(chuàng)立者之一。他在代表作《企業(yè)、合同與財務(wù)結(jié)構(gòu)》中進(jìn)一步發(fā)展了產(chǎn)權(quán)理論,提出了“不完全合同”理論。
上世紀(jì)80年代中期,哈特為契約理論的一個新分支領(lǐng)域研究作出了根本性的貢獻(xiàn),這一研究針對解決不完全契約的重要問題。因為契約不可能指定每一種可能性,新分支理論闡明了控制權(quán)的最優(yōu)分配,即契約的哪一方應(yīng)該在哪些情況下作出決定。哈特對不完全契約的研究結(jié)果揭示了企業(yè)的控制權(quán)和所有權(quán),并對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幾個領(lǐng)域、政治學(xué)及法律等產(chǎn)生了重大影響。他的成果為人們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,可以研究如哪些公司應(yīng)該合并,債務(wù)和股權(quán)如何適當(dāng)組合,以及學(xué)校或監(jiān)獄等機(jī)構(gòu)應(yīng)該私有還是公立等問題。
另一位獲獎?wù)弑咎亍せ裟匪固亓_姆則是一位知名的微觀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家,他還曾經(jīng)是芬蘭著名企業(yè)諾基亞的一名董事。1978年,霍姆斯特羅姆在斯坦福大學(xué)獲得博士學(xué)位。此后他曾先后擔(dān)任美國西北大學(xué)凱洛格管理學(xué)院副教授和耶魯大學(xué)經(jīng)管學(xué)院埃德溫-J-拜內(nèi)克管理學(xué)教授。現(xiàn)在他是麻省理工學(xué)院保羅-薩繆爾森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教授,同時還兼任麻省理工學(xué)院斯隆商學(xué)院的教授。此外,他還擁有瑞典斯德哥爾摩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院和芬蘭漢肯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院的名譽(yù)博士學(xué)位。
上世紀(jì)70年代末,霍姆斯特羅姆通過模型示范了一個主體應(yīng)如何為一個代理設(shè)計最佳契約,而代理的部分行為不能被主體所察覺到。這一信息原則精確地詮釋了該契約如何將代理人的薪酬與績效相關(guān)信息聯(lián)系起來。霍姆斯特羅姆運(yùn)用這一基本模型,展示了最優(yōu)契約如何慎重權(quán)衡風(fēng)險與激勵。在隨后的研究工作中,霍姆斯特羅姆將這些研究成果推廣到實際應(yīng)用中,以更好地解決現(xiàn)實中的一些問題,例如代理人在很多任務(wù)上付出努力,但主體僅能觀察到一部分;還有團(tuán)隊中的個別成員可以搭便車享用其他人的努力成果等問題。
契約理論在現(xiàn)實生活中的運(yùn)用
在今年的諾貝爾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獎揭曉后,許多人也對契約理論在現(xiàn)實的經(jīng)濟(jì)活動中能夠起到的指導(dǎo)作用產(chǎn)生了興趣。在諾貝爾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獎評委會成員托馬斯·舍斯特侖姆看來,今年的諾貝爾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獎得主們對契約的理論研究有廣泛的實用性,比如怎么給一個公司的執(zhí)行總裁或工人們定工資的,比如國家政策制定者如何衡量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與環(huán)境保護(hù)等問題,如何有效規(guī)避因目前眼光的局限而帶來的隱患等。
具體到中國經(jīng)濟(jì),也有專家認(rèn)為,契約理論的研究成果可以給中國企業(yè)參與國際并購提供指引。例如中國銀行斯德哥爾摩分行行長郝連才就認(rèn)為,談到中國企業(yè)在“走出去”全球化發(fā)展,尤其是在成熟市場經(jīng)濟(jì)體的投資,“契約意識和合同管理能力,是‘基本功'”。
郝連才舉例稱,北歐法律環(huán)境完善、市場化程度高,市場主體的契約意識都非常強(qiáng)。不管是企業(yè)合作,還是員工雇傭,對合同的精細(xì)化約定和契約的遵從,都非常重視。中國企業(yè)在利用西方市場通用的契約規(guī)則,進(jìn)行公司治理結(jié)構(gòu)、激勵制度的契約安排方面,還是有許多地方需要重視和注意的。有一些身邊的企業(yè),在并購后由于與職業(yè)經(jīng)理人間的契約安排過于簡單,出現(xiàn)了比較大的“委托-代理”沖突和法律糾紛,大大加大了并購后的整合和經(jīng)營風(fēng)險。
對此,郝連才建議,中國企業(yè)應(yīng)當(dāng)重視法律事務(wù)和對契約的合理利用;重視培養(yǎng)熟悉國際市場規(guī)則、了解當(dāng)?shù)匚幕膶I(yè)化人才;重視對外投資項目的運(yùn)營管控和規(guī)則約束,并借助專業(yè)中介和服務(wù)機(jī)構(gòu)的專業(yè)智力,提高市場契約管控能力。
(相關(guān)資料綜合自人民網(wǎng)、新華網(wǎng)、北京青年報等媒體)
(編輯:陳姝)
